唐力:在时空里,与死者协商
感谢重庆市作家协会,感谢重庆文学院,前几日召开了“纪念汶川大地震十周年暨唐力《大地之殇》诗歌研讨会”,感谢各位文学界的朋友。
有朋友问我,为何要选择这样一部重大的灾难主题来写作?我在这里,讲述自己是如何创作这本诗集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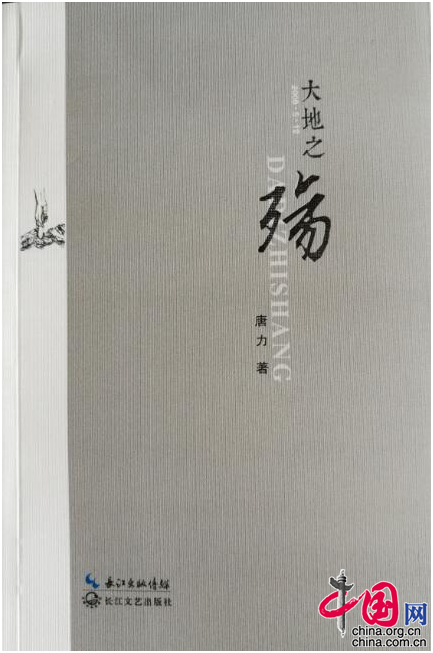
一
这是一部沉重的诗集。
是的,这的确是一种对作者的挑战。
面对巨大的灾难,文学何为?诗歌何为?我们如何去告慰死者?如何去抚慰生者?这也许是我写作《大地之殇》的初衷。
写作中,我常常产生怀疑,有时也受到朋友的置疑:在浩如烟海的地震诗歌中,我再写作这样的一部作品,它的意义何在?这是应时之作?或是内心的由衷之作?我们民族是否需要这样的作品?
我想,对于这样一场大灾难,特别是大灾难依然在地球上不断出现,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思考?当面对灾难缺席,我们是否也是一种罪恶?
对于这样的大灾难,应该产生出伟大的诗歌,深刻反思的诗歌,写出生命与死亡交锋的悲壮,写出信心与绝望的奋争,写出人类之痛……
我相信,会有更多的人做出努力,会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奔走,我仅是这个队列中的一员。
十年,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,在弹指一挥间,就来到了今天,但曾经悲惨和哀伤的情境,仿佛就在昨日,作为一个作家,永远不能忘怀。
在创作中,我也走访了映秀镇、汶川、都江堰、彭州等地,亲临了地震遗址,灾后重建现场,去还原记忆,真切的体验和直观的感受。
在5•12汶川地震之后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幸存者,作为一个幸存者,回溯这场灾难:
遇到很多困境,比如记忆与遗忘的困境:我们既不能遗忘,又不能时常记起。对于生者来说,这是一个两难。对于写作者来说,也是两难。

二
我在写作的时候曾一度陷入困境。
比如道德的困境:写一个事件,就如重新揭开了疮疤,这对受难者是不是第二次伤害?
我在后记中写到:“与生者对话,尤其困难。因为中间,隔着死者。”因此写或不写,仿佛变成了不断往复的诘问。
在写作中,我只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协商者的角色,与死者协商、与生者协商。在协商中获得某种允诺,从而使写作能够得以继续。
还有写作的困境:地震造成的苦难,触目惊心,易于表现。但写重建也困难得多,得寻找新的典型的场境、细节,并加以重新的叙述。
因而写作极其缓慢,最终形成了现在以组诗和小长诗的面貌,表达了大地的伤痛,生命的涅槃和重生、家园的重建、心灵的重建、精神的重建。去追寻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力。
这就是现在桌上的这本诗集《大地之殇》。

三
在时空里,与死者协商。
在5•12汶川地震之后,我也是一个幸存者,或者说,我们都是幸存者。虽然,我们没有真实地经历那一场灾难,但我们的心灵却实实在在地经历过它了。在那些日子里,电视画面、图片、文字、声音等等,都让我们真实地经历了。与他们一起,我们同样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,经受了那些疼痛、苦难、恐惧、悲伤……因而我们都是幸存者。
然而考验还未结束,漫长的心理复苏仍然在时间中绵延。在受伤之后,我们能不能重新获取一个完整无缺的、完美的心灵?
我们既不能遗忘,又不能时常记起。对于生者来说,这是一个两难。我们不能遗忘灾难,遗忘逝去的亲人,也不能沉浸在过去的伤痛之中。
时间是治愈伤痛的良药,但也许它又不是。
5•12是中华民族的灾难,也是整个人类的灾难。
灾难还在继续,海地大地震、智利大地震、日本大地震,还在给人类带来新的伤害。
灾难还在重临,而生存还将继续。
我们依然要寻找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力。
正如地下的死者,他们虽然在废墟之下,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黑暗中的抗争,他们依然在地底下奋争:
他们分散的爱,依然依靠着泪水
血肉,结成一个整体
埋在地底深处
抵抗着,大地的灾难

四
当我写作这些,我仅是一个对话者。
作为生者,我站在了他们的对面:死者的对面。也许在我纸张的背面,就站着他们,他们用或痛苦或悲伤或恐惧的眼神注视着我,注视着这些文字。
这让我有时难以下笔:我是否写下愧对他们的文字?
我面对的不是一个人,而是庞大的群体。据资料显示,汶川地震:
遇难:69227人。
失踪:17939人。
受伤:374640人。
作为对话者,我感受到他们的力量,也感受到我的孤单。
巴蜀之地,也是我的家乡,人们会让“端公”、“乩仙”等通过神秘的仪式,与逝世的先人沟通、对话、诉说,这实际上是与死者协商。现在想来,我们在高大、阴暗的堂屋,或者在野外、细雨中的坟前祝祈、祷告,也是一种与死者协商的过程,在冥冥中达成某种协议。因此,作为一个对话者,我的叙述是与他,与他们协商的过程。最终,我由强势的述说变成了沉静的表达。
那些词语,也默不作声
我知道,迫使它们哑默无声的
是石头上面,缭绕着的信息:逝者的信息
逝者痛苦的灵魂
有时候死者,他们直接开口说话。“没有了生命的转动/时间也是孤单的”,在《汉旺镇:时间之伤》,我写到时间、生命、死亡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,它们相互纠结,而又相互穿透。我相信,只有生命,才会让时间充满活力,它那滴答的声音,听起来才悦耳,动听,它有着一种力量,那是超越灾难的力量。
死者依然在我们的对面,又与我们遥相呼应:
用他们的血脉
穿透纸张和空间、时间
与大地上的亲人,遥相呼应
——《死者花名册》
与死者协商,这是对死者的敬重,对死亡的敬畏。当我行走在那片土地上,或是在这些字里行间,我感受到他们的存在:
众多的灵魂,在我身体中飞翔

五
与生者对话,尤其困难。
因为中间,隔着死者。
他们:受难者,或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(原谅我在这里用委婉的说法),或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园,或者失去了很多亲人……在对话中,无疑的,这些逝去的人会回来,隔在中间。
在写作的过程中,我读到一篇文章,给我触动很大:
“他们会一次次“强迫”幸存者回忆自己的恐怖经历。每被追问一次,孩子们就会产生不安全感。王静雅希望这些经历过地震的人,应当忘掉自己不幸者的身份,而不要一遍遍强化这种角色。”
这使我不得不停下来,自问:我是不是这样的“强迫者”?在写作苦难中,我是不是在加深自己的罪恶?我是不是让这些不幸者,再度成为不幸者?
因此,我们在绝望中树立希望,尤其重要。我看到了,两个妇女正忙着搅拌用于建房的河沙、水泥,我相信,她们身上正体现了生存之力:“太阳,在她们的睫毛上,升起”,或有那些用仅存的手,建造房屋的人,他们打开的手:“在颤抖中,山河在血脉中浮现”。
我们应该用“生存来告慰死者”,这才是最为重要的。要让生的意志,穿透死亡和苦难。
这些关于汶川地震的诗作,是地震陆续写作的,持续了一个特别漫长的时间。沉哀来自于痛苦之后,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说:“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,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”。写作中,我常常产生怀疑,有时也受到朋友的置疑:在浩如烟海的地震诗歌中,我再写作这样的一部作品,它的意义何在?这是应时之作?或是内心的由衷之作?我们民族是否需要这样的作品?
我想,对于这样一场大灾难,特别是大灾难依然在地球上不断出现,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思考?当面对灾难缺席,我们是否也是一种罪恶?
对于这样的大灾难,应该产生出伟大的诗歌,深刻反思的诗歌,写出生命与死亡交锋的悲壮,写出信心与绝望的奋争,写出人类之痛……
我相信,会有更多的人做出努力,会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奔走,我仅是这个队列中的一员。
但我会铭记,站在死者的对面,作为一个虔敬的对话者,与他们协商……
血脉依然在承继
灵魂依然在字面上
栖息,永不消逝评论

